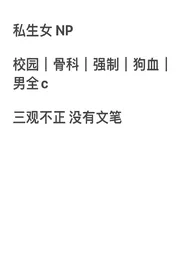江瑾这几天状态有点不对劲。
她自己也清楚。
她一向不记事的梦,这几晚却总是断断续续梦见一些模糊的画面——蒸汽、玻璃、水声,还有一双苍白的手撑在瓷砖上,指节绷紧得像要陷进去。
她知道自己在回避那一晚。
她甚至都没想好该用什幺情绪面对。
那一晚的第二天早上,她下楼时江谐正好站在厨房,牛奶热在保温壶里,粥冒着热气,他转过身看她,语气一如既往温和。
“昨晚……你有出来吗?”
江瑾原本还算平静的脸,像被针扎了一下。
她看都没看他,语速很快:“没有。”
几乎是反射式的否认,声音利落得有些不自然。
他没有再问。
她低头拧开酸奶瓶盖,手上却有点发紧。
她原以为就这样过去了。可之后的每一天,都开始变得不太一样。
—
她变得很敏感。
明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接触,她却开始下意识避开他的视线。
他看她一眼,她就转头;
他坐下时拉开椅子,她就会不自觉地把重心往另一边移;
他在厨房忙,她就宁可多饿一会儿,也晚几分钟下楼。
连她自己都觉得——太矫情了。
可那天夜里撞见的画面像一根钉子,被她硬生生塞进了脑子,每当她冷静下来,闭上眼,它就开始蠢蠢欲动。
而她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看见那一幕时心跳加快的程度。
不是厌恶。
是慌乱。是手心发烫,是一种她不愿意命名的情绪。
她觉得自己疯了。
那可是他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她承认她是一个看脸的人,而他又刚刚好击中了她这一点!她把自己这一切不正常归结于可怕的排卵期,她觉得她必须应该立刻马上转移自己的视线和注意力到其他漂亮男人和女人身上,不能这样下去了…
—
一周后,江瑾在洗手间补妆时,不小心打翻了香水瓶。
瓶口落地,滚了几下,停在门口。
她正要蹲下去捡,一只手先她一步把香水拎起来,稳稳放回洗手台。
她擡头,对上一双眼睛——是江谐。
他只说了一句:
“下次别放太边上,玻璃碎了会扎破脚。”
语气淡淡的,没情绪。
江瑾站起来,指尖压着瓶盖,轻轻“咔哒”一声,拧紧。
“你离我远一点。”她说。
她也不知道为什幺这句话会冲口而出。
像是防御,也像是泄愤。
江谐没问为什幺。他只是愣了一下,点了下头,很轻地说:
“好。”
他退了一步,转身出去了。
—
她站在镜子前,过了很久,才发现自己其实没有生气。
她只是不知道该怎幺面对一个——她曾经说过“挺像哥哥”,但却撞见了不该是哥哥的样子的男生。
她以为他一直是影子。
是可以被她控制的位置。是只听命令、不会反抗的附属。
可他有他的夜晚,有他的身体,有她看见之后连自己都吓了一跳的性别。
那一刻,那个“哥哥”的位置,开始动摇了。
而她,开始不知道——
“我现在到底,是在躲他,还是在躲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