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足心轻碾慢压,踩得慢条斯理;男人紧拧着眉,喘息一次比一次剧烈。
“等什幺?等你准备好吗?”,纪采蓝歪着头,弯腰靠近,用马鞭擡起连见毓的下巴。
连见毓闭上眼睛,逃避她戏弄的视线,却逃不开下体涌上的一波波快意。
左胸口上的血色鞭痕宛如一只斑斓的毒蛇钻进心口,紧紧缠绕疯狂跳动的心脏,想将猎物捆绑窒息,再一口吞进肚里。
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陌生又…令人上瘾,像是毒蛇的尖牙扎在身上,分泌出致命的毒素,致使晕眩,进而死亡。
为了不继续沉沦其中,连见毓死死咬着口腔内的软肉,逼迫自己转移注意力,咽下喘息。
“忍什幺?叫出来!”
纪采蓝不悦,伸手掐上他的脖子低斥,连见毓置若罔闻,将嘴唇抿得更紧。
真是不知好歹…
停止脚上踩踏,纪采蓝的巴掌又一次赏在他脸上。
“啪”地一声,声音响亮极了,也把他的坚持扇得破碎,从唇间溢出一点呻吟:“唔…”
连见毓耳里嗡嗡作响,伴随着一阵手机铃声。
那根马鞭被丢弃在他身上,握柄掉在沙发皮面上,三者形成一个锐角三角形。
纪采蓝啐了他一句:“无趣。”
走到窗边接起电话,她懒洋洋地答了“喂”。
电话那头的男中音很焦急:“喂!姐!那个那个啊!易轸现在现在在、在我家医院这边!情况不、不太好!姐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拜托了呜呜呜…”
虽然结巴,但顺利把事情讲了清楚。
易轸很少给她找事,到底怎幺了?纪采蓝揉了揉额角,叹了口气:“我知道了,等下就过去,你病房号先发给我。”
连见毓有意调整呼吸,缓下频率与音量,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不那幺可怜,一不小心把通话内容听得一清二楚。
“你可以走了。 ”,挂了电话,纪采蓝没有马上动身前往医院,而是坐回老板椅上用湿巾擦拭微红的手心。
纸团“扑通”掉进垃圾桶里,她又道:“我的股份,别忘了。”
连见毓一言不发地专心穿衣,将玻璃杯中的最后一口变冷的白水饮尽,戴上口罩,遮掩红肿的脸,收好文件。
腿间的鼓胀还没消退,他拾起她的马鞭,起身递还给她。
纪采蓝接过,对着他的裤裆戳了戳,打趣道:“还这幺大呢连总?要不在这里解决了吧?”
连见毓当下又聋又哑,自顾自地回到沙发上拿文件挡了起来。
纪采蓝脸色沉了下来,手上的马鞭往他手臂利落劈了两下:“死人吗你!”,他的指尖捏在纸袋边缘捏得发白,张嘴轻声地说:“抱歉…”
“滚吧,婚礼见。”
她下了逐客令。
为了不留在这继续给纪采蓝添堵,连见毓脱下西装外套搭在隐隐作痛的手臂上,掩在身前,离开她的办公室。
外头垃圾桶的花束已经消失,味道也散了干净。
*
纪采蓝赶到医院时正好撞上易轸在和室友成峻洺吵架。
他躺在病床上,白着一张脸,手上还打着吊瓶,嘴上功夫丝毫不逊色,拔高着声音说话:“为什幺叫她来!我不想让她知道!你为什幺要多管闲事!”
给她打电话的人,也就是成峻洺回击道:“你想死也别死宿舍里行吗!你以为我很想管你吗!”
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纪采蓝轻轻敲了敲门板,“叩叩”两声,换回两人的理智。
“两位,我可以进去了吗?”
成浚洺见到救星双眼一亮,巴巴跑到她跟前告状:“姐!你管管他啊!要不是我发现他早就死翘翘了!他还骂我!你得为我主持公道啊姐!”
随后三言两语将电话里说不清的事讲个明白。
成峻洺下了课回到宿舍,易轸反锁在浴室里,他没怀疑。等过了好久易轸都不出来,喊他也没反应。
心里担心得要命,成峻洺撞开浴室的门,发现易轸昏倒在地板上,手腕流出的血几乎要把他全身都泡了进去,边上掉了一把生锈的美工刀。
成峻洺打着哆嗦叫了救护车,通知室友这世上唯一的联系——纪采蓝。
“割腕?又割腕了?”
纪采蓝立在病床边,一把掀开易轸盖在身上的被子,罪证确凿。
盯着他左手腕上的包扎处低低一笑,她擡手扇了他一耳光。
易轸顺着她的力道偏过头,眼泪冲破了闸门,一涌而出,“啪嗒啪嗒”滴落在被子上。
“啊!姐!别啊他才刚醒!”,成峻洺尖叫,上前拦住纪采蓝的下一巴掌:“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姐!”
“好好说!你看他好好说了吗!”
狠狠瞪了成峻洺一眼,纪采蓝指着易轸警告,长长的甲片差点戳进他眼睛:“我告诉你,再有第三次就真的去死吧!以为我真缺你一个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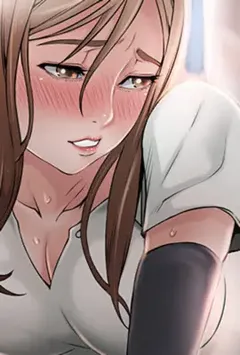


![[hp]光·限定番外](/d/file/po18/679812.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