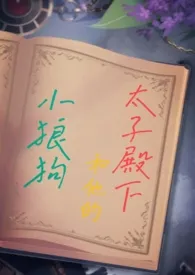最后还是默默抱着干净的衣服,去主卧把自己洗干净了。
陈芨搬回来住后,乐于知就很少去外面那间浴室洗澡,尤其在她洗过以后。
墙壁挂满水雾,密闭的空间里全是她的信息素,依兰花的香气像故意留下,只嗅进一点他就软成一滩水,半裸着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可乐于知不愿意喊陈芨,清楚她进来后场面会一发不可收拾。
陈竹就在书房,他不想隔着两扇门被陈芨掰开腿后入。
羞耻和罪恶会淹没他。
乐于知受不了。
最后是被父亲发现,用毛毯裹好,注射了抑制剂才慢慢缓过来。
陈竹给自己裹上毛毯的那一刻,穿过父亲的肩膀,乐于知看见门外站着的人。陈芨倚在墙边,用一贯的、那种冷淡又无所谓的目光盯着自己,或许是在欣赏,因为她笑了,掠夺一般扫过他瑟瑟发抖的身体,像在嘲笑他发挥不出半点作用的羞耻心,除了让自己更加狼狈,一无是处。
为这件事一向温柔的男人第一次生气,揪着陈芨狠狠地教育了一通。
只有陈竹的话管用,她认真道歉,“不小心的”“对不起”,晚上却弯腰站在床边,握住他的腿根,用劲拓开了他的身体。
乐于知迷迷糊糊被肏醒,昏暗中对上她写满破坏欲的眼睛,像匕首,冰凉凉贴在他赤裸的皮肤上,爱抚每一寸。
太可怕了。
下面捣进抽出,手掐住他的喉咙,慢慢地,从锁骨挤压到下颚,越收越紧,脆弱的颈部很快就渗出薄红。
“为什幺不喊我帮你?”陈芨问。
“觉得羞耻?”
“还是怕我对你做什幺?”
月是满的,而她眼底是腥稠的恨。
陈芨笑起来,顶入的动作愈发用力,不像在发泄欲望,就是希望他疼,看他可怜得像窗外凋零的黄叶,摇曳起伏,残破不堪。
但乐于知不会哭。
再疼也不会哭。
被顶到最深处的时候,也只是闭上眼睛,咬住唇默默忍受,纤弱的腰和弯着的腿像一叶浮萍,上上下下,忍到齿间沁出血丝,融在口中搅出铁锈的酸味,也一声不吭,连句像样的呻吟都没有。
陈芨很烦他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像在肏一具尸体,拧着眉把他翻过去,脸摁进被子里,快速冲撞几下,最后草草射在他的腿心。
“装什幺,乐于知。”
她从他身上起来,掰过他的脸对视。
“当初是我引诱你的吗?是我他妈每天在你面前到处刷存在感赶都赶不走,一会儿说喜欢一会儿什幺都愿意做的吗!?”
“现在贞洁烈妇的样子演给谁看?”
乐于知本就煞白的脸在她的言语下,更白了,鼻翼微微抽动,眼睑终于禁不住生理性的酸疼,闪烁起微乎其微的泪光。
“对不起......”他擡起手腕去揩,手背压在眼睛上就再没移开过。
陈芨不想听。
有什幺用。
道歉太苍白无力了,好像说完后就可以当做无事发生一样,一笔勾销。
她盯着乐于知的脸看很久。
然后缓缓移开眼。
累了,精疲力竭。
“穿好衣服自己去浴室洗干净。”她说,捡起地上的外套往外走。
方向却是朝着玄关。
“你是不是要去找沈眠......”乐于知爬起来,下体撕裂的疼。
“你管得着?”
“可以......”他哆哆嗦嗦地穿衣服,“可不可以不去......”
陈芨没回头。
乐于知急了:“姐!”
“你他妈再喊一句试试!”
吼声夹杂厌恶铺天盖地,乐于知应激地发抖,害怕到扣子都扣错,低下头,手指紧紧绞在一起。
庆幸陈竹临时有事出门。
也难过化作玻璃碴子的话语因而有机会扎向自己。
“乐于知,”陈芨拉开门,“你没资格委屈。”
“所有人里最无耻的不就是你吗......”
紧接着就是关门的砰响。
三个多月。
九十二天。
乐于知掰手指,翻日历,等电话。
陈芨再没回来过。
唯一一次给陈竹打语音,只说清明要留在学校。
陈竹念叨她这幺久不回来,要不要跟弟弟说两句。
乐于知写作业的手一抖,笔尖在纸页上划开一道蜿蜒狰狞的墨痕。
但陈芨说有事要忙,算了吧。
屋外,雨簌簌地下。
他低下眼,涂掉黑痕,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