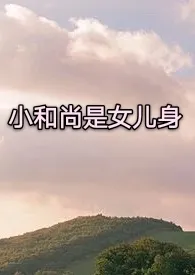由于清楚记得先前走过的路,加之步城君路程中万分谨慎,一行人顺利返回遭逢怪物的河谷,然而几人并未靠近,仅是待在远处观望。
巍峨岩壁如刀削般纵切直下,衔接底部的绵长河道,潺潺流水穿过层层叠叠嶙峋奇石,深入至尽头的幽黑河洞,浓雾弥漫间望去,洞口如咧开了嘴的巨兽,教人不由得心生畏怯。
「就是那里,」步城君对何焉说道,视线转而望向其他人,「你们留在这,我先进去里面探查情况,去去就回。」
杭愉一听急忙出声叫唤:「师兄!」
步城君微笑,拍了拍杭愉的脑袋,一派轻松道:「别担心,师兄我可是既怕死又怕疼,不会出事的。」
边说着,步城君边起身准备离开,忽闻清冷的声音自身侧响起,「我和你一起去。」
步城君动作停顿,诧异地看向正展开雪白素伞的何焉。
「此地危机四伏,结伴同行不仅彼此有个照应,也能让杭姑娘稍微安心点。」何焉说道,迳自迈开脚步朝洞穴方向而去。
「可是──」
「我会尽量不拖累你的。」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
眼见何焉不理会他,步城君连忙和牧芸年交代了几句,便匆匆追赶上前急道:「我是希望你能留下来照顾她们!」
毕竟李飞鸳把话说得那么白,没法寄望那家伙在危急时会伸出援手,相形之下何焉似乎更加可靠;但何焉显然没有步城君那么多顾虑,只淡淡提出自己的看法。
「牧姑娘心思周密,伤患在侧,行事定会比平时更加小心;至于李飞鸳,虽然说话不大好听,但若是真出了事,我想应该也不至于袖手旁观。」
「不管怎么说,多留个人总是好的……」见劝不动这固执的少年,步城君无奈叹息。
何焉沉默不语,思绪早已飘远了去,此刻心中只有百般疑惑翻腾,好奇心挠得胸口搔痒难耐却不知从何问起──
你是步城君?《天洐秘事》系列的主角步城君?那话本写的是你曾经历过的事?舒毓蓉是你的道侣?玉人阁的王璃同你又是何种关系?
……不行,无论怎么问都太唐突,而且初识不久便贸然刺探他人私事着实失礼,他压根儿做不来。
想起尉迟修对《天洐秘事》也颇有心得,何焉一度想不管不顾地直接透过拾音铃询问,即使再次以身体做交换亦在所不惜;可瘴岚谷内四处暗藏凶险,他怕打扰了师兄办正事,内心兀自纠结得紧。
他跟在步城君身后,急行军似的一刻不停沿河岸前行,直到进入河洞后才缓下脚步。洞窟幽暗,水声泠泠,一股怪风挟带着香甜气味,霍然如无形凶兽猛地欺身而上,狠狠辗压过何焉的神志。
步城君立即出声提醒,可何焉听不清他说了什么,脑袋受到巨大冲击,伴随着一帧帧不属于自己记忆的陌生景象涌入,耳边仿佛响起模糊人声。
这是什么?
无数人影跪伏于繁茂巨树前,虔诚而卑微地膜拜、祈祷,高耸祭台之上献予神明的不是酒水果品或血食牲畜,而是一名未着寸缕的精壮男性,繁重枷锁牢牢桎梏其四肢,教他拚死挣扎亦逃脱不得。
环绕祭场的火焰骤然转为青紫,杂沓人声随之止息,幽暗中传来悦耳的咯咯娇笑,肥硕树藤逐渐延伸至祭台,化身为三名赤身裸体的美艳女子,步履翩跹绕着祭品来回审视。
何焉心惊──那正是他曾在梦境见过的女妖!
发色嫣红如血的妖物攀上祭台、柔美身段贴紧了羊羔般的祭品,极尽狂放淫浪的姿态,像是点燃何焉体内的火种,下腹滋生莫名热潮,溢开了滚烫的沸水般一路灼烧,后知后觉意识到身体有些失控,就好像……好像初遇七师兄那时!
步城君的身影在眼前晃悠,何焉没来由地感到口干舌燥,颤抖的灵魂叫嚣着想扯开那身衣帛、撕咬肌肉、吮食精血……!
他仓皇失措,脚步虚浮一退再退,趁着步城君独自往前探查、全副心神都在注意四周的情况时,何焉狼狈不堪地逃离。
待步城君回过头,身后早已不见人影。
何焉感到全身发烫、吐息紊乱而急促。
由于一心远离步城君,他慌不择路地跑,竟不知跌跌撞撞逃到了何处,只双手抱着红颜,夹紧了腿全身乏力,不断反思自己怎么打进入瘴岚谷以来便状况频频、老是造成别人麻烦。
体内的汹涌情热掀起阵阵涟漪,荡开血液中被灵药压制的雪脂树毒,意识渐渐朦胧不清,勃发欲望同黏腻湿意搅成了一滩脏污泥泞,如影随形附著于身,使他寸步难行。
何焉拄着红颜伞瘫坐在地,身上不知何时浮现一圈圈细密的银色咒文,虽然隐约感觉到这些东西束缚住那企图篡夺身躯的力量,但两相牵制之下,心神渐趋疲弱,越发难以抵御喧嚣欲火的煎熬。
恍恍惚惚间,何焉嗅到一股子浓郁的雪脂树香扑鼻而来,不祥预感油然升起,微小的摩娑声由远而近逐渐放大,当何焉察觉时,手腕、腰部与双腿,已被大量漆黑丝线牢牢缠缚!
「唔……!」
何焉不停挣扎,面前赫然惊现一张煞白的女子脸庞!那张脸镶嵌在黑暗中,紧贴着何焉与其四目交会。
霎时间心跳停摆、整个人如坠冰窟!
女子面上毫无表情,如墨杏眸瞠圆了死盯着何焉半晌,随后细瞇着弯起,红艳艳的小嘴开阖着发出轻喘,明明是张绝美脸庞,却处处散发出非人的怪诞。
即使精神濒尽溃堤、身子抖得不成样,何焉仍试图触碰拾音铃;但女人的脸微微擡起,那一头乌缎长发缠紧何焉、进而钻入他衣襟底下,拽下练远的白玉铃铛,当着何焉的面绞成了一块块碎石。
祂扯开唇角露出甜笑,好似在向何焉昭告唯一的生路已绝。
处在极端惊惧与欲望焚烧拉扯之间,何焉陷入无比混乱,耳边回荡着垂死残喘,生死交会之际,他竟只遗憾没能和步城君多聊上几句……
「滚开。」
黑影瞬起、惊风急掠,缠捆何焉的浓密妖发唰地应声断裂,那白如死尸的美人脸瞬息间亦皮开肉绽,还没弄清发生什么事,撕裂喉咙般的凄厉惨叫已响彻洞窟里外!
「嘎啊啊啊啊──!」
那妖物疯了似哀号,藏匿于黑暗里的原形彻底暴露──丰腴柔美的女体,下半身却连接着巨大交缠的雪脂树藤,祂双手掩住脸上不断涌出白色汁液的伤口,痛不欲生地挣扎。
何焉浑然未觉身旁的纷乱,意识迷蒙间,一只眼熟的长尾玄色大鸟映入眼帘。
牠停在何焉身侧,不一会儿便扑腾着漆黑羽翼,振翅飞向角落的一抹颀长身影。那人一擡手,黑鸟登时凭空化作溅开的墨痕,悄无声息地融入无尽的阒暗里。
人影穿过尚未散去的墨晕,也不知是身患重疾、抑或精神不济导致的疲怠,他微微斜着头长发披散,拖曳着有气无力的步伐走近何焉,一袭艳调子的绣花大氅招摇醒目得很,与周身散发的委靡气质显而易见不搭调,活像具吊着悬丝、死气沉沉的华丽傀儡。
匍匐在地的女妖狠瞪来人,凶戾目光几乎化作有形的刀刃,欲要活剐了眼前的青年;然而此人身上处处渗满毒液般的危险气息,教无端恐惧生生掩盖过翻腾恨意,只得趁对方不察悄悄遁没至阴影中,逃离男人的视野。
申屠砚从头到尾倒是没瞧过那怪物一眼,满目只有那倒地的少年──素伞白衫丽人,形貌姝艳雌雄难辨,与蒲邑舟描述的完全相符。
他蹲下身扶起何焉,才入怀便察觉异常。纤细身板下刚烈灵气脉动,压制住躁烈不定的魂魄,烈火灼烫的燠热硬是将清丽面容烧出令人心荡神驰的娇态。
……淫邪入体,经施咒定魂,本该万无一失。
修长手指轻点何焉眉心,一阵凉意沁入额间,驱散了脑海中千回百转的古怪幻象,再无喧嚣着欲夺占肉体的不速之客。
他敞开绣花大氅将何焉密实裹入怀中,拨开小孩儿额前被汗水浸透的浏海,慢慢靠近耳畔,轻声道:「腿,张开。」
何焉已被欲火折磨得失了魂,听见男人低沉的耳语,只以为又是哪个师兄发话、得乖乖遵照,乖巧地从了这荒诞不经的指示。
媚毒险恶,毒性发作唯一药可解。虽有世俗方内之人坚守清白宁死不屈,但抛开食人礼教拘束,胜在药方唾手可得,只消一场酣畅淋漓的云雨巫山,便再无后顾之忧。
怀里的二形子很是配合,开着腿像小孩儿被把尿似的,由着人朝裤缝里探也不懂得反抗。指尖往湿淋淋的嫩穴深了戳、肆意抠挖掏弄,弄得淫水四溅流进臀缝,裤底都湿漉漉的,也只晓得发出情动至极的低喘。
申屠砚未曾见过二形之人,略有些好奇,一边玩着穴、一边搓捻那瘫软着的玉茎,竟丝毫不觉厌恶。那小东西生得白嫩秀气,手指磨蹭着便颤颤巍巍地抖,不一会儿得了趣,才越发地张扬硬挺。
瘦骨嶙峋的大手虚握着茎身上下套弄,堵在穴里的手指亦不曾撤出,只在里头荒淫无度地搅,搅得汁水四溢。何焉快要喘不过气,上衣整整齐齐地,下身裤装半褪、双脚绷直,颤得缚身的银链子琅珰作响。
瞧何焉面上漫开的病态薄红,好似女子红妆般艳丽,申屠砚不自觉俯首咬上那片通红耳根、舔进了耳洞。小孩儿受不得半点刺激,瞬间蜷紧脚趾,揪着申屠砚衣袖仰首惊慌失措地叫,点点泪珠蜿蜒爬过面颊,红透了的脸蛋满是初登极乐的无所适从。
男人垂着头看不清表情,沾满浓精的手凑近嘴边,一下一下细细地舔。混杂两形之躯的阳精阴精,味淡而不腥,不知不觉一点不剩地下了肚。
二形子刚泄身,仍是浑浑噩噩,夹紧了双腿、身子蜷缩成团,一副再不让任何人触碰的抗拒姿态。
毒性未解,申屠砚动作变得强硬,手掌强行撑开何焉腿根,解了裤裆就将下身那硬实挺长的肉刃顶端往湿软处挤。
欢愉余韵犹存,被逼着再次张腿迎来野蛮的进犯,何焉仓皇挣脱申屠砚的怀抱,双膝着地爬着想逃离,可身后大掌随即死死扣住了腰,巨大阴影罩住何焉,烫热阳物不由分说钻进腿心,又是顶又是辗,凿出大片泛滥成灾的湿黏。
饱胀龟头蹭过后庭、滑入穴口,来来回回几次后,大手绕过腰肢握住少年瘫软的小肉桩,同他精气勃发的硕大肉茎贴紧了,猛烈挺动着往死里摩,摩得小炉鼎腰塌了、腿软了,两瓣臀肉都红了大半,还要被扳过身子正对着他,继续蹭那淅沥沥吐着稀薄精水的小小孔洞。
「走开……走开!我不要……不要……」
何焉被欺负得狠,本就敏感的阴茎生得不如寻常男子,哪里挨得住接连蹂躏,一门心思想逃;申屠砚不允,犹自巍然不动,握着粗大肉杵将前端抵住渗着甜水的穴,慢悠悠捣了进去。
何焉猝然躬起身,下腹一阵几欲逼疯人的酥麻,贯穿脊背直抵脑门。
耳边传来沉声喟叹,散乱长发如墨液般倾倒至何焉胸前,摆荡出一层覆一层的黑色涟漪。何焉被撞得不停摇晃,热杵捣送出激溅四溢的水波,水又化作了潮,掀起滔天巨浪要将他浸溺于深不见底的欲海。
欲海生于欲,亦是阴阳灵息汇聚的海,自交合处奔泄而出的灵气涌入丹田、流向周身各处,好似服用了极致珍稀的大补圣品,历经一次纯净灵气淬体。
此时的申屠砚完全不见先前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腰胯动得厉害,一下下抽送得又快又狠,直把何焉肏得再次失了神,无助挠着男人腰腹的精实肌肉,时不时叼住自个儿的手指,无从舒缓激烈情潮。
求饶抗拒的哭喊老早变了调,声声都似蘸满糖蜜,比舌尖残留的精水还甜。
潜伏的雪脂树毒已将残存理智侵蚀殆尽,教那清冷少年彻底化作一头春情勃发的野兽,浪叫得响、腰扭得欢,起伏颠簸的腰肢因濒近欲望巅峰而不停颤动,肉壁一抖一抖地缠绞着塞满女穴的男茎,像张能吮人魂魄的嘴,生生往欲海再掀起一波蚀骨销魂的震颤。
申屠砚轻吐了口气,一个深顶后忽地缓下动作,又慢又重地堵着穴儿搅,小孩儿禁不住这般不疾不徐的狎弄,急喘着踮起脚尖挺胯,纤细腰杆来回摆动使劲吞吐着阳根,似是拿男人作淫乐器具,自个儿玩得快活无比。
明明是为了解媚毒,眼下却解得两人都要成了瘾,一时半会愣是抽不了身。
申屠砚撩开额前长发,苍白面色淡然自若,不见半点欲望痕迹,可那折腾百来回的孽根火热惊人,猛然一下凿进最深处,将媚红肉洞撑到极致,肏得何焉不止抽搐,扭着身躯仿佛又沾上什么要命的毒。
这看似无穷尽的春宵大梦终该清醒。
男人慢慢退开身、又再给堵回去,重复了好几回,每回都撞得凶狠,还留下不少东西在二形子的小肚子里。
何焉再也叫不出声,迷蒙间似被强行灌入一大池又稠又湿的浓墨,黏糊糊地,用底下那张小得可怜的嘴。
.


![[综]女主她总在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d/file/po18/683292.webp)